| www.11hunli.com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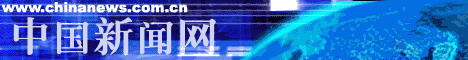 |
|
張潔:我的痛苦,其實就是我的財富 文/劉家中
給一個文字極講究的人寫印象記,真是件極恐怖的事。如果那個人又是一個歷過人間滄桑、看破了紅塵的人,當然是比簡單的班門弄斧更更更地難以下筆。 認識張潔幾年,總是隔三差五地煲些長長的「電話粥」,都是些關于家長里短的無主題變奏。因了這篇賴不掉的文債,才逼得我這個懶笨人挖空心思地想想張潔是個怎樣的人。 張潔是個喜歡低調的人。今年2月某報紙關于兩會的報導,有一張背影的照片,我拿著報紙打電話問她,她笑著承認:「是我,我不愿意上鏡頭,說好不讓他們拍,沒想到還是被偷拍了。」這樣的事很是打著張潔的痕跡。出書的時候,因為有重名作者的緣故,她不得不附上自己的照片,但總是嚷嚷著:小點兒,再小點兒。 張潔是個嘴上說不再相信愛情卻永遠也不會真正放棄愛心的人。她以《愛,是不能忘記的》出道,經歷了數不盡的坎坷,如今年過花甲的她總是把「愛是不能指望的」像是誓言又像是提醒一樣掛在嘴邊。現在的她走在街上看到兩個年輕人手拉著手,她會為那個女孩子的愛情擔心,晚上她會在電話里告訴我:「如果你出問題了,別怕,我是你的窩。」她總讓我想起那段禪說:一個小和尚向老和尚學習禪宗,被老和尚棒喝,小和尚頓悟。所不同的是,我這個小和尚總是冥頑不化,而張潔也從來不會像那個老和尚「痛下狠手」。相反,眼前這個老和尚知道那個終極在哪里,只是因為不忍,才并不刻意地點醒小和尚,反而一再地說,「不醒就不醒吧,如果醒了,別怕別怕,有我。」──她痛過,所以她怕別人再痛。 張潔是個超堅強的人。我曾經無意中翻出她寫在1986年的一篇散文:《我的第一本書》,里面有一句話像是讖語那樣讓我驚心。她說:「當我摩挲著我第一本裝幀粗糙、紙張低劣的書的時候,我悟到,我的痛苦,其實就是我的財富。」我驚詫的是即使在她生命表面最輝煌的那個時期,她所背負的苦痛就已是常人無法承受的了,但比起那時,她生命中注定要承載的更大的痛苦還在1986年之后等著她,還遠遠沒有到最高潮,還遠遠沒有完結……從那時到現在的十幾年的更大的苦痛沒有人知道她一個人是怎么扛過來的。 張潔是個永遠的「憤青」。她對政治的狂熱從《沉重的翅膀》一直保持到現在,但認識她的人誰也不會把她和成熟沉穩的革命者形像聯系在一起。「我小時候就想當一個堅貞不屈的革命者,你懂吧。怎么說呢,犧牲,獻身。就喜歡這個,不管對愛情還是對一個合理的社會,獻身。我覺得『獻身』這兩個字特別棒。」她的更像是小布爾喬亞的政治熱情,讓她在作為政協委員參政議政時像個不諳世事的青年人,沒有顧忌地滔滔不絕:「什么是理想社會我也說不出來,但看見不合理的事情我就要提出批評。在理想的社會里,應該尊重人家的人格。包括吃喝拉撒睡也包括在人的生的權利里。我覺得這是最起碼的一點。」所以每年的兩會,她都會有一大堆提案交上去,哪個居民院兒的下水道多年堵塞都會被她寫上去。 不認識張潔的人總是把她和女性作家和女權主義放在一起,認識張潔的人都知道她會對這兩個詞大為光火:「我為什么要賣這個『女』字?不賣這個『女』字,就不能成為一個好好寫書的人嗎?如果是個自立的女人,就應該在這平等的基礎上進行競爭。我真干出來是我的能力,不是因為我是女人,或者我長得漂亮。如果那樣,對男人公平嗎?一個人,要是心臟健康的時候,你不覺得它嘣嘣嘣嘣在跳,你非得是真的有病的時候,才會心率過速啊,停跳啊,或者是狹窄,堵塞。所以你如果意識到你是女人,你也有點問題。」 張潔是個惟美而挑剔的人。她喜歡美食,喜歡漂亮的工藝品,喜歡看好的演出。對不喜歡的人和事,她也會沒有顧忌地像個男人那樣地罵「粗口」。她的喜好純粹而且率直,好像在她那里從來沒有「同行是冤家」的概念,每每看到同行有了精彩的作品,她都會興奮地到處打電話大段大段地念給別人聽。「我希望我在讀者心目中是一個好作家,我的長項是悟性好,細節用的好。不過你看了最近王安憶的作品了嗎?真好,還有張承志的……還有余華的……還有王朔的……還有史鐵生的……還有葉兆言的……真好真好。」談她創作的話題幾乎每一次都是這樣拐了彎兒。 久久沒有在文壇露面的張潔目前的工作是對她創作長達十年的長篇小說《無字》進行最后的修改,預計今年底就可把三卷本出齊。1998年底已經出版的《無字》第一卷讓很多讀者感到驚訝──在人們已經習慣了精神產品也像可口可樂一樣成為商品的時代,居然還有人在做這樣嘔心瀝血的事情──在一個長篇當中,不計成本地把激情和爆發力一貫到底,從靈魂中重新摳開的傷口讓人觸目驚心。張潔說:現在的我像個賭徒一樣,把所有的輸光了。離婚,貓死了,我媽去世,生病……都弄得我消沉的……我這輩子就剩下寫作這一件事。這是我惟一所愛,惟一的寄托。以前的作品我總是為別人而寫,從《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和《無字》以后,我要為我自己寫,為了給自己一個交代。而且我真的覺得越寫越好,這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就像你都輸光了,但你還有一個房子沒賣,沒典當出去,多好啊。我知道《沉重的翅膀》那種東西應該寫,但是我再不浪費我的生命了。我和出版社談好了,書出來后第一不簽名售書,第二不開作品研討會──這些熱鬧對于我來說都是沒有用的了。 此文石墻背景的那張配圖是張潔最喜歡的一張照片,她拿給我一是因為那上面的石頭是她最喜愛的,二是因為她自己在上面占據的位置很小──一如她的低調。結束此文時我忽然心中一動,找出《無字》第一部,翻到第4頁,果然上面有關于這石墻的文字。附后──解讀她的千言萬語還是她自己的文字更為合適。 「每每面對那石墻,便會在溟蒙中看到有銘文在那墻上時隱時現,銘刻著與她休戚相關而又不可解讀的文字。起先那銘文像是剛剛鐫刻上去的,然后經雨雪風霜越來越深地蝕入石墻,倒好像那石墻如血肉之軀在不斷生長,漸漸地將那些文字嵌入自己的身軀。那是一種莫測的,說有形又不可見,說無形又很具體的力量,日夜鐫刻不息的結果。」 ■張潔 國家一級作家、現任中國作家協會理事、北京市作協副主席、北京市政協委員。1992年被美國文學藝術院選為該院榮譽院士。主要作品:《愛是不能忘記的》、《沉重的翅膀》、《方舟》、《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無字》。 摘自《北京青年報》2001.3.1 |
|
.本網站所刊載信息,不代表中新社觀點。 |
